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发现自己活成了一辆车,一辆属于全班的、24小时待命的、永不收费的“公共汽车”。

这不是什么比喻,这是我的日常。座位不用抢,因为每个“乘客”都知道,这车上永远有他们的专属位置。路线也是他们定的,今天张三要去打印店,明天李四忘了带U盘,后天王五的电脑需要我远程救急——鸣笛,发车,风雨无阻。我这台人形“公交”,唯一的任务,就是确保每一位“乘客”都能满意地到达他们的目的地。
至于我自己的油耗、我自己的保养、我自己想去的方向?谁在乎呢?公交车有权利拥有自己的目的地吗?
一趟名为“有求必应”的死亡循环路线
起初,我甚至有点享受这种“被需要”的感觉。每一次“谢了啊哥们”,都像一枚廉价的勋章,短暂地满足着我那可怜的、渴望融入的虚荣心。我以为我在广结善缘,在为自己铺路。后来才发现,我铺的不是路,是一条单向的、通往自我耗竭的“不归路”。
借笔记?整本拿去,我的复习计划?不存在的。小组作业没人做的部分?放着我来,我的睡眠?算个屁。谁跟对象吵架了,我是情感垃圾桶;谁生活费花超了,我是移动ATM。我像个陀螺,被一根根名为“帮个忙”的鞭子抽得飞速旋转,停下来就是我的不对。
最可笑的是什么?是“乘客”们下车时那句轻飘飘的“谢谢”,甚至有时候连“谢谢”都懒得说,一个眼神,一个点头,仿佛我天生就该为他们服务。他们心安理得,而我,在这辆名为“我”的公交车里,看着窗外本该属于我的风景一闪而过,内心只剩下发动机空转的巨大轰鸣。我开始频繁地“emo”,在深夜里,这辆破车的每一个零件都在哀嚎。
“乘客”无罪,是我亲手递上的“永久免费卡”
我曾怨恨过每一个把我当工具人的“乘客”。但当我某天凌晨三点帮别人改完一份无关紧要的报告,对着镜子里那张憔悴的脸时,我突然想通了。
怨他们?他们有什么错?
是我,是我亲手把这辆车的钥匙交了出去。是我,在每一次犹豫着想说“不”的时候,都因为害怕对方失望的眼神而选择了“好的”。是我,用一次次的“没问题”和“我来吧”,亲手给每个人都办了一张“永久免费乘坐卡”。
这根本不是善良,善良是有锋芒的。我这算什么?我这叫**“价值感的预付式悲剧”**。我像个赌徒,把我的时间、精力、情绪一股脑地推上赌桌,就为了赌一个“被喜欢”“被需要”的虚名。结果呢?人家玩完就走,留我一个烂摊子,连句“再会”都显得多余。我甚至不是他们的备胎,我是他们的公交车,召之即来,挥之即去,廉价、方便,且从不抱怨。
熄火,下车,老子不干了!
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,是一次期末。我通宵帮三个人整理了复习资料,结果第二天自己发着高烧进了考场。考完后,其中一个人在走廊上大声炫耀自己的高分,路过我身边时,甚至都没问一句“你考得怎么样”。
就在那一刻,我这辆破车,彻底熄火了。
引擎冷却,车门紧锁。那个瞬间,我感到的不是愤怒,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。去他妈的“好人缘”,去他妈的“被需要”,老子不干了。
改变的开始,是痛苦的。当我第一次拒绝了别人的请求,我看到了对方错愕的、甚至带点鄙夷的眼神。我的心像被揪了一下,那种被集体抛弃的恐惧感瞬间袭来。但我忍住了。我说出那个“不”字之后,迎来的不是世界末日,而是一片属于我自己的、宁静的空地。
渐渐地,找我的人少了。那些所谓的“朋友”,在发现我这辆车“收费”了、“停运”了之后,便迅速地寻找下一个“免费公交站”。我的世界清净了。我开始有时间看自己想看的电影,有精力为自己的考试做准备,有心情去关心自己的喜怒哀乐。
我不再是一辆公共汽车。我成了一个人。一个有权决定自己要去向何方,有权拒绝搭载不想载的乘客的人。我终于明白,真正的自我价值,不是来自于你为别人做了多少,而是来自于你有多尊重和珍视自己。
所以,如果你也感觉自己快要变成一辆“公交车”了。听我一句劝:请立刻、马上、毫不犹豫地——拉下刹车,拧掉钥匙,然后潇洒地走下车。
外面的世界,风光正好。走路,比当一辆任人驱使的破车,要爽得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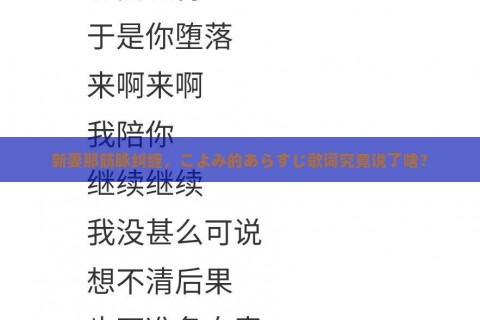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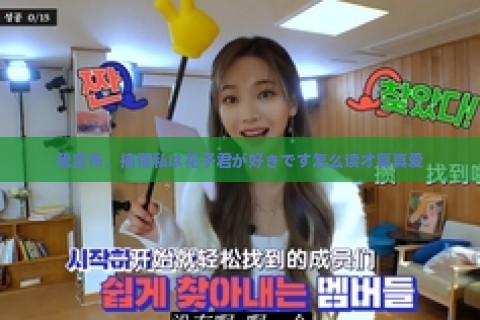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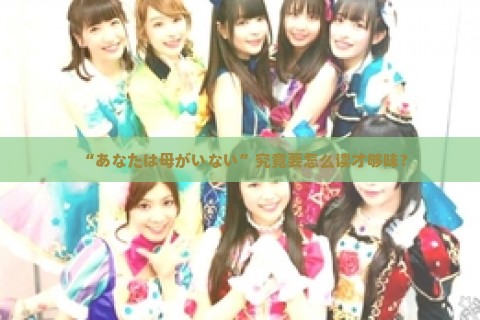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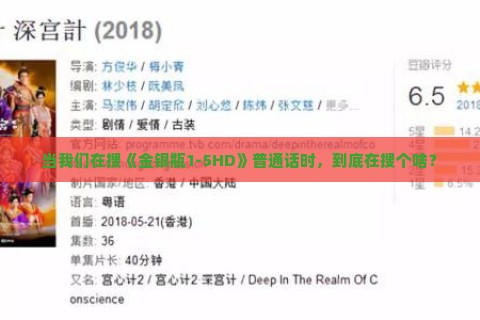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